1927年10月23日,陈宜张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的周巷镇,现隶属于宁波市慈溪市。周巷位于杭州湾大桥的桥南,由北过桥向西拐弯至庵东,再往西行约十公里即周巷。周巷镇的通大桥和大通桥之间的河北岸,长了一棵高大的古樟树,树的附近居住着同宗的十几户陈姓人家。清代末年,他们共同经营一家“同春染坊”,所以这些家庭之间以及陈氏以外人士,便称对方为“樟树下同春XX房”,陈宜张的高祖父排行第三,故被称为“樟树下同春老三房”。说陈宜张书香门第,也不算太典型,陈宜张的祖父陈少慕(1874— 1938)是晚清秀才,曾祖和高祖也都读书识字,所以陈家可称书香人家。
陈宜张的曾祖和祖父是两代单传,父亲陈登原有兄弟四人,二弟早殇,三弟陈叔陶,四弟陈季涵。陈宜张有一个姐姐和三个弟弟,是同春老三房的第五代人。
1904年(光绪30年)陈少慕在31岁时考上秀才。
次年,延续干余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寿终正寝,开明而有远见的陈少慕对此早在意料之中。
陈少慕对长子陈登原在学识方面的要求严格。有一次把儿子关在书房内,逼他阅读《资治通鉴》。儿子生气了,坚持不读,但被锁在房内也很无聊和无奈,便随便翻开这部大部头书看看。起初他是略加浏览,但几经翻看,他逐渐对书中的内容发生兴趣,便主动地逐字逐句通读起来。他后来入东南大学攻读历史系,成为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与“闭门逼读”不无关联。陈少慕很有眼光,他知道拥有科学知识的重要,所以竭尽全力,培养自己的三个儿子,都成为国立大学毕业的优秀人才。
1927年农历9月28日,陈宜张这个属兔的胖小子,在同春老三房出世,给久未添丁的陈家带来了欢乐。陈少慕替这个长房长孙取名陈宜张,希望孙儿将来彰显家门,张扬家风,53岁的陈少慕对陈家后继有人甚为欣慰,自然地成为长孙的第一位“庭训”老师。
他教孙儿学习古文和背诵《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结合诗、文讲解,穿插讲述相关的历史故事,所以陈宜张听得很有兴趣。他替孙儿批改作文,用心细致,有圈有点有批语,批语多系鼓励之词。陈宜张有一次在作文中,引用“若不胜追兵之逐者”一词来形容台风过后,天空云彩的快速飘逸。陈少慕为此句之运用巧妙适当大为欣赏。当时,陈宜张是八岁的孩提,能有如此深刻的国学领悟,可见平时学习是很勤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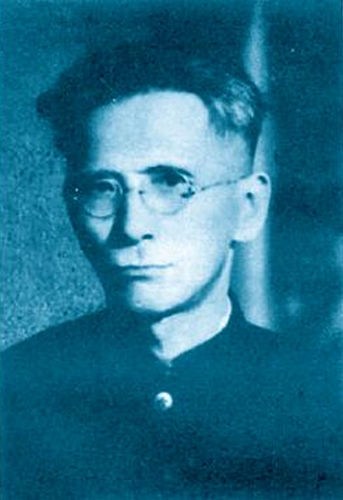
1959年陈登原在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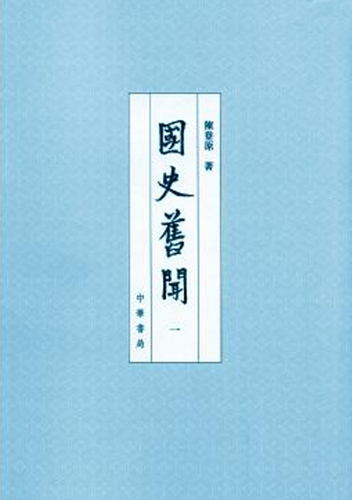
陈登原著《国史旧闻》书影。
每年夏天和家人围坐纳凉的时候,便是陈宜张向祖父和父亲学习古文、古诗和文史知识最合适的机会。他能背诵自居易的《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那时他不懂这些缠绵悱恻诗句的意境,但也觉得有点伤感。此时,陈登原便给他讲解开元、天宝之治和安史之乱的历史,说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陈宜张的记忆超常,88岁的陈宜张院士至今还可背出120句,840个字的《长恨歌》诗句。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陈登原在讲解白居易的《琵琶行》时,讲到自居易与元稹的政治主张和文学见解都很一致,友情特别深厚。当说到元稹在病中得知白居易被降职后写的诗句:“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时,陈登原不禁情为诗动,高声朗读起诗句来。诗意激起父亲感情的投入,让陈宜张从小感染到诗言志和诗句渲染的魅力。
陈宜张读得较多的是《古文观止》中的古文。他喜欢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尤其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他把这篇散文印刻在脑海之中,以致在2012年85 岁那年,到理发室理发时,会对安徽滁州籍的理发师,即兴背诵《醉翁亭记》。他告诉理发师,“欧阳修描写的正是你的家乡滁州。”陈宜张兴奋地用略带宁波口音的普通话摇头晃脑地背诵:“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 滁籍理发师虽然不明白这位慈祥老人朗诵的是什么意思,但知道是描写他的家乡的美景,感到这是对他的尊重,所以心生好感和谢意。他下意识地眼睛盯着老人,他的头也不由自主地摇晃起来似乎表示:“颇有同感。”当然,在为陈老整理皓首时,自然细致入微,梳理银发“一丝不苟”。
陈宜张喜欢刘禹锡的《陋室铭》。他读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时,祖父告诫他说:“做人,环境虽差,但重要的是要有德,有志向,有操守,有了这些做人的品格,环境再差也无所谓,陋室也就‘何陋之有’了。”尽管他当时还不能完全体会这些警句里的深意,但他潜移默化地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他说:
优美的古诗词,可以陶冶情操,培养情感,教人道理,有时还会给人开拓思路和启迪,就以欧阳修《醉翁亭记》为例,作者运用清晰的描述,首先放眼“环滁皆山”的大背景、大环境,由此引出“西南诸峰”,再到诸峰中的“深秀者琅琊”,呈现“水声潺潺的酿泉”,最后才使“临于泉山上的醉翁亭”呼之欲出。如此丝丝入扣的描写,体现了缜密的逻辑,而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缜密的逻辑,需要抽丝剥茧,去伪存真.(注:除非另有特别说明,全书陈宜张引语,均来源于陈宜张访谈、2013年3日14日26日,4月12日,9日16日和10月17日。上海,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全书同,余注略。)
陈宜张从小得到的文学奠基和受到的文史诗词方面的训练,使他在今后几十年的科研实践中,善于把文学思维融入科学探索而丰富了科学的内涵,使科学和文学能水乳交融。父亲给陈宜张兄弟们讲述中国古代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和古希腊芝诺“游矢不动”的故事,使陈宜张自幼感受到逻辑推理的魅力。陈宜张回忆说,父亲在茶余饭后的谈话,每日功课的督促,传授的文学、历史、科学知识以及做人的道理,使他们兄弟们终身得益。
陈宜张的父亲陈登原长期在外地任教,有时母亲也随父亲同行,所以,幼年的陈宜张和大姐宜振、二弟宜和,便由祖父母照料抚养。陈宜张自幼爱动脑筋和贪玩,经常在顽皮一天后,满身脏泥回家。他偷偷地溜回家后,第一件事是看祖母的脸色,观察老人家有否生气。
1996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初二,陈宜张夫妇和儿子大庞回故乡重访周巷旧宅,回忆童年趣事时,陈宜张心情激动,曾赋诗《忆周巷樟树下故居》以志。
三更梦醒想前尘,樟树同春栖此身。
雪压梢枝冬烂漫,花引蛱蝶夏丽绚。
堂前击弹虾背屈,宅后捕蝉猿臂伸。
汗出淋漓顽皮后,进门偷看祖母嗔。
1938年的盛夏,一天下午,陈少慕全身乏力,不思饮食,连续上吐下泻。经中医诊治和西医注射强心针,均无效果,至次日凌晨便撒手西去,终年64岁。后来得知,他是染患霍乱,当时如能输入生理盐水,可以挽救,但周巷那时没有这个医药条件。陈宜张的父亲陈登原对其父的无法救治,深感无奈和无助。当时,他想他的儿子如果是医生,那该有多好!
开明的秀才祖父
1927年10月23日,陈宜张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的周巷镇,现隶属于宁波市慈溪市。周巷位于杭州湾大桥的桥南,由北过桥向西拐弯至庵东,再往西行约十公里即周巷。周巷镇的通大桥和大通桥之间的河北岸,长了一棵高大的古樟树,树的附近居住着同宗的十几户陈姓人家。清代末年,他们共同经营一家“同春染坊”,所以这些家庭之间以及陈氏以外人士,便称对方为“樟树下同春XX房”,陈宜张的高祖父排行第三,故被称为“樟树下同春老三房”。说陈宜张书香门第,也不算太典型,陈宜张的祖父陈少慕(1874— 1938)是晚清秀才,曾祖和高祖也都读书识字,所以陈家可称书香人家。
陈宜张的曾祖和祖父是两代单传,父亲陈登原有兄弟四人,二弟早殇,三弟陈叔陶,四弟陈季涵。陈宜张有一个姐姐和三个弟弟,是同春老三房的第五代人。
1904年(光绪30年)陈少慕在31岁时考上秀才。
次年,延续干余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寿终正寝,开明而有远见的陈少慕对此早在意料之中。
陈少慕对长子陈登原在学识方面的要求严格。有一次把儿子关在书房内,逼他阅读《资治通鉴》。儿子生气了,坚持不读,但被锁在房内也很无聊和无奈,便随便翻开这部大部头书看看。起初他是略加浏览,但几经翻看,他逐渐对书中的内容发生兴趣,便主动地逐字逐句通读起来。他后来入东南大学攻读历史系,成为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与“闭门逼读”不无关联。陈少慕很有眼光,他知道拥有科学知识的重要,所以竭尽全力,培养自己的三个儿子,都成为国立大学毕业的优秀人才。
1927年农历9月28日,陈宜张这个属兔的胖小子,在同春老三房出世,给久未添丁的陈家带来了欢乐。陈少慕替这个长房长孙取名陈宜张,希望孙儿将来彰显家门,张扬家风,53岁的陈少慕对陈家后继有人甚为欣慰,自然地成为长孙的第一位“庭训”老师。
他教孙儿学习古文和背诵《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结合诗、文讲解,穿插讲述相关的历史故事,所以陈宜张听得很有兴趣。他替孙儿批改作文,用心细致,有圈有点有批语,批语多系鼓励之词。陈宜张有一次在作文中,引用“若不胜追兵之逐者”一词来形容台风过后,天空云彩的快速飘逸。陈少慕为此句之运用巧妙适当大为欣赏。当时,陈宜张是八岁的孩提,能有如此深刻的国学领悟,可见平时学习是很勤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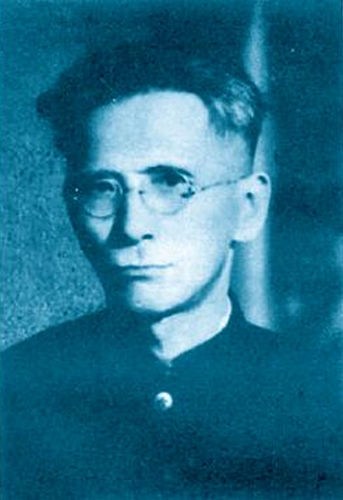
1959年陈登原在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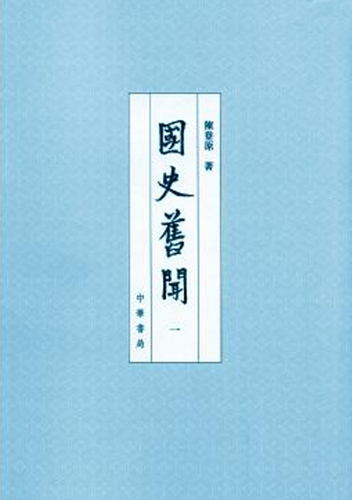
陈登原著《国史旧闻》书影。
每年夏天和家人围坐纳凉的时候,便是陈宜张向祖父和父亲学习古文、古诗和文史知识最合适的机会。他能背诵自居易的《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那时他不懂这些缠绵悱恻诗句的意境,但也觉得有点伤感。此时,陈登原便给他讲解开元、天宝之治和安史之乱的历史,说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陈宜张的记忆超常,88岁的陈宜张院士至今还可背出120句,840个字的《长恨歌》诗句。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陈登原在讲解白居易的《琵琶行》时,讲到自居易与元稹的政治主张和文学见解都很一致,友情特别深厚。当说到元稹在病中得知白居易被降职后写的诗句:“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时,陈登原不禁情为诗动,高声朗读起诗句来。诗意激起父亲感情的投入,让陈宜张从小感染到诗言志和诗句渲染的魅力。
陈宜张读得较多的是《古文观止》中的古文。他喜欢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尤其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他把这篇散文印刻在脑海之中,以致在2012年85 岁那年,到理发室理发时,会对安徽滁州籍的理发师,即兴背诵《醉翁亭记》。他告诉理发师,“欧阳修描写的正是你的家乡滁州。”陈宜张兴奋地用略带宁波口音的普通话摇头晃脑地背诵:“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 滁籍理发师虽然不明白这位慈祥老人朗诵的是什么意思,但知道是描写他的家乡的美景,感到这是对他的尊重,所以心生好感和谢意。他下意识地眼睛盯着老人,他的头也不由自主地摇晃起来似乎表示:“颇有同感。”当然,在为陈老整理皓首时,自然细致入微,梳理银发“一丝不苟”。
陈宜张喜欢刘禹锡的《陋室铭》。他读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时,祖父告诫他说:“做人,环境虽差,但重要的是要有德,有志向,有操守,有了这些做人的品格,环境再差也无所谓,陋室也就‘何陋之有’了。”尽管他当时还不能完全体会这些警句里的深意,但他潜移默化地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他说:
优美的古诗词,可以陶冶情操,培养情感,教人道理,有时还会给人开拓思路和启迪,就以欧阳修《醉翁亭记》为例,作者运用清晰的描述,首先放眼“环滁皆山”的大背景、大环境,由此引出“西南诸峰”,再到诸峰中的“深秀者琅琊”,呈现“水声潺潺的酿泉”,最后才使“临于泉山上的醉翁亭”呼之欲出。如此丝丝入扣的描写,体现了缜密的逻辑,而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缜密的逻辑,需要抽丝剥茧,去伪存真.(注:除非另有特别说明,全书陈宜张引语,均来源于陈宜张访谈、2013年3日14日26日,4月12日,9日16日和10月17日。上海,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全书同,余注略。)
陈宜张从小得到的文学奠基和受到的文史诗词方面的训练,使他在今后几十年的科研实践中,善于把文学思维融入科学探索而丰富了科学的内涵,使科学和文学能水乳交融。父亲给陈宜张兄弟们讲述中国古代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和古希腊芝诺“游矢不动”的故事,使陈宜张自幼感受到逻辑推理的魅力。陈宜张回忆说,父亲在茶余饭后的谈话,每日功课的督促,传授的文学、历史、科学知识以及做人的道理,使他们兄弟们终身得益。
陈宜张的父亲陈登原长期在外地任教,有时母亲也随父亲同行,所以,幼年的陈宜张和大姐宜振、二弟宜和,便由祖父母照料抚养。陈宜张自幼爱动脑筋和贪玩,经常在顽皮一天后,满身脏泥回家。他偷偷地溜回家后,第一件事是看祖母的脸色,观察老人家有否生气。
1996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初二,陈宜张夫妇和儿子大庞回故乡重访周巷旧宅,回忆童年趣事时,陈宜张心情激动,曾赋诗《忆周巷樟树下故居》以志。
三更梦醒想前尘,樟树同春栖此身。
雪压梢枝冬烂漫,花引蛱蝶夏丽绚。
堂前击弹虾背屈,宅后捕蝉猿臂伸。
汗出淋漓顽皮后,进门偷看祖母嗔。
1938年的盛夏,一天下午,陈少慕全身乏力,不思饮食,连续上吐下泻。经中医诊治和西医注射强心针,均无效果,至次日凌晨便撒手西去,终年64岁。后来得知,他是染患霍乱,当时如能输入生理盐水,可以挽救,但周巷那时没有这个医药条件。陈宜张的父亲陈登原对其父的无法救治,深感无奈和无助。当时,他想他的儿子如果是医生,那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