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德:我是气动弹性专业的工程师
原标题:管德院士:我不是科学家,我是气动弹性专业的工程师
“我不是科学家,我是气动弹性专业的工程师。我不敢谈什么科学理论成就,我的目标是尽力把工程实际中的飞机设计工作做好。”
——管德

潜心科研的飞机设计师
1932年7月12日,管德出生在北京,父亲尹凤鸣是他生活和学习的启蒙老师。
尹凤鸣是清末留日武备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毕业。回国后曾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官。1925年3月13日,被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授予陆军少将军衔。但他厌恶官场的龌龊,很快脱离军政两界,靠房租收入维持一个大家庭的生计。日寇入侵,北平沦陷后,尹凤鸣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到日本人管制的学校读书,所以管德的小学、初中学业都由家庭教师教授。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管德考入北京五中。1949年高中毕业,他报考了清华大学、北洋大学两所大学的航空系,均被录取,最终他选择了清华大学。

1949年,管德大学时期照片
1952年,管德根据上级要求提前毕业,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他在局办公室调研科担任了局刊《通报》的主编,并以出色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局领导的肯定。
1956年8月,二机部四局发布《关于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决定在112厂、410厂分别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任命局第一技术科科长徐舜寿为飞机设计室主任设计师,叶正大、黄志千为副主任设计师。
徐舜寿提出飞机设计室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四局领导很快批准了徐舜寿的设计方案,新飞机定名为歼教-1型飞机。
管德到飞机设计室工作后,徐舜寿交给他的第一项技术工作是完成歼教-1理论外形的计算。
为使飞机具有良好的气动特性,机翼、机身等外形均为曲面,表面必须平滑光顺。这就需要通过计算得出多个截面的曲线,而每一个曲线都是由一段一段的二次曲线来模拟的。每一段曲线需要三个点,列成三元一次联立方程式进行计算。20世纪50年代,新成立的飞机设计室仅有两台电动计算机,因为有更重要的计算任务,所以对于外形曲线的计算,管德只能用手摇计算机计算。
这项任务技术上并没有太高要求,但计算繁琐,工作量很大,终于管德等几位技术人员完成了歼教-1飞机的外形数据计算任务。通过这一项枯燥、单调的任务,徐舜寿认定管德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很好的发展潜力。为解决飞机颤振问题、培养气动弹性力学方面的技术尖子,徐舜寿从108名、平均年龄22岁的技术人员中选择了管德进行气动弹性研究。
这是在二战中开始引起航空工程界普遍关注的一个跨多学科的新领域。由于飞机结构不可能是绝对刚性的,飞行中必然发生弹性变形,这种弹性变形会影响飞机的气动特性,使空气动力随之改变,进一步导致弹性变形,构成结构变形与空气动力交互作用的气动弹性现象。随着飞机飞行速度提高,气动弹性会显著影响飞行器的操纵性和稳定性,严重时甚至会使飞机结构破坏,造成严重的飞行事故。
在收集了国外的相关资料和专著后,徐舜寿带着管德等开始了对非定常空气动力学的钻研。对于管德来说,学习这些前沿航空科学技术并非易事。他在清华大学只读了三年,而且大量时间被繁忙的政治活动占据。在毕业以后的四年中,他主要从事的又是行政工作。但管德利用落后的计算手段,很快算出了歼教-1飞机的颤振速度。结构力学专家黄玉珊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算颤振速度。
迈出可贵的第一步以后,管德更加潜心于气动弹性力学的研究。
我国气动弹性专业的奠基者和带头人
1960年底,中共中央批准国防部第六研究院(航空研究院)成立。1961年8月,由空一所、112厂飞机设计室等合并而成的第一研究所(六院一所,后改称601所)成立,管德担任新组建的气动室颤振组组长。

六院一所成立之初,管德(后排左四)与研究室科研人员合影
1963年,管德被聘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第16专业组理论分组成员。这个学术团体由钱学森担任组长,代表着当时中国空气动力学的最高水平。
1964年8月,管德担任六院一所气动室副主任,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尉军衔。也是在这一年,歼-8飞机开始研制。管德主持了歼-8飞机研制中的气动弹性专业设计计算和试验,创造了国内该专业领域多项第一次。
在成功完成了歼-8飞机各项颤振计算后,他又进行了国内第一次飞行颤振试验。通过颤振分析,可以达到控制机翼重量的要求,这是歼-8飞机突出的技术成果之一。
1979年7月,航空气动力协作攻关办公室气动弹性组(“7210”第五专业组)成立,管德担任组长。
从那时开始,管德一直承担航空预先研究中气动弹性力学领域的组织工作。曾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套可用于超声速飞机设计的气动弹性计算和试验方法,总结了《高速歼击机的气动弹性分析》,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9年12月30日,歼8白天型设计定型资料审查时合影(右起:邱宗麟、管德、钟敏昭、顾诵芬)
1979-1981年,管德主持研制了“航空结构动力分析系统HAJIF—Ⅱ”。它可以进行结构的固有动力特性((固有频率、振型)的计算,以及带主动控制系统的飞机颤振和突风响应计算。
管德提出了这个系统的总力学任务书,来自5个研究所的人员参加了此项工作。系统中设计了31条固定流程,以适应不同飞机的计算需求。

1979年5月,管德(左)与冯钟越赴美考察期间合影
始终坚持气动弹性领域的研究
1980年9月4日,歼-8Ⅱ飞机正式立项。1982年底,601所完成了飞机结构图纸。为加速歼-8Ⅱ型飞机研制进程,1982年9月,上级决定将管德调入松陵公司(今为沈飞公司)任第一副经理兼总工程师。
1983年,管德兼任歼-8 Ⅱ飞机研制现场总指挥、试飞领导小组组长。他按照系统工程方法,使歼-8 Ⅱ飞机首飞时间大大提前,为此荣立航空工业部新机首飞一等功。

1984年,管德参加歼-8Ⅱ飞机首飞评审会议
1985年,管德任航空工业部科学技术局局长,后任航空工业部总工程师、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航空研究院院长。
1985年底,管德调任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后兼任党委副书记。他推行矩阵管理,改进计划工作,使飞行员培训、空中管制等一些原来薄弱的系统得到加强。他积极主动组织和参与民航系统的体制改革,拓展融资渠道,加快民航机队、机场的拓展与技术改造,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民航事业的发展和全行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在行政领导职务不断变换,肩头责任愈来愈重的情况下,他始终没有丢弃自己从事的气动弹性专业研究。管德一直希望能在航空工业系统组建一个专门的飞机气动弹性研究所,带出一支具有国际水平的专业团队,向更高目标冲刺。
1985年,管德到北京赴任之初即受聘兼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由他编写或主编的《非定常空气动力计算》《气动弹性试验》与《飞机气动弹性力学手册》至今仍为飞机设计单位气动弹性设计人员的首选参考资料,同时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飞机设计气动弹性专业的经验总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国内最早从事气动弹性专业研究的学者之一陈桂彬这样评价管德:“管德很敬业。他对气动弹性理论有深刻的理解,在工程实践中有丰富的经验。在国内气动弹性领域,他有很大的贡献。”
熟悉管德的人对他有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位性格刚毅、敢讲真话的人,一位执着于自己从事的专业的人,一位为事业默默奉献的人。
顾诵芬院士曾经多次说到:管德在颤振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来讲是领先的,没有人这么下功夫弄这个东西,干这个活没名、没利。他担任领导后也绝不错过到西德去学习的机会,在那里,他也就是做一个普通技术人员的工作,但他在理论和应用方面有所建树,做出了明显的成绩。
在飞机设计领域,气动弹性专业对飞机安全至关重要,从事气动弹性研究的科研人员总是站在总设计师身后,做无名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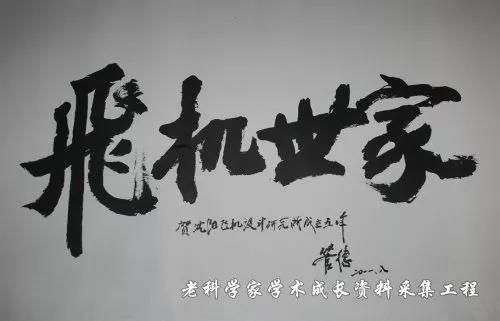
2011年8月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成立50周年,管德为此题词“”飞机世家
2018年1月9日,管德院士因病在北京逝世。
《弟子规》中写道:“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管德院士身材修长、气宇轩昂,属于“貌高”者,但他赢得人们的敬重则是由于他的“行高”,他襟怀坦荡、刚正不阿、志存高远、成就卓著。
管徳的人生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最好的诠释和传承,体现出了一名真正共产党员的理想和精神追求。
文:师元光,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原常委、研究员
本文图片来源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网络版)


